周勋初先生治学方法举隅
2021-11-19 02:00:50华夏高考网周勋初先生非常重视传授治学方法,从1983年9月开始,曾多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过“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课程,所写五篇讲义,后均编入《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是周先生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该生在周先生的指导下,将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的问学笔记,整理成了《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1年增订再版)。该书主要内容也是谈治学方法。周先生自2011年9月至11月,应邀写了二十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在《古典文学知识》连载,后编为《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以下简称“经验谈”)一书,由凤凰出版社于9月出版。周先生的治学经验非常丰富,我仅就治学方法谈点學習体会。
一、 从目录学入手
早在大学二年级时,周勋初就上过胡小石先生的“工具书使用法”课,这自然使他认识到目录学对读书治学的重要性。后来他师从胡先生修读副博士研究生课程,學習《楚辞》,写作《九歌新考》初稿,显然得益于目录学知识。他曾说过:“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从古籍书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饶宗颐先生的《楚辞书录》,此书后附论文索引,很多是发表在民国时期旧杂志上的论文。”于是他利用到北京探亲的机会,“按照索引的提示,到北京图书馆期刊室中借阅”,“上至王逸、朱熹等人的著作,下至苏雪林、何天行等人的论文,都曾钻研。”(《周勋初文集》第7册第370页,以下简称“文集”)这对他撰写《九歌新考》当然大有帮助。
南大中文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原由罗根泽先生上,罗先生后因病重中辍,遂由周先生接替。周先生在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过程中,还编了本适合学生自学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专著篇目索引》。这为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奠定了基础,该书多次出版,还被译成韩文与日文,可见深受欢迎。
周先生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注意利用目录学知识来为自己服务。如周先生为了做好《唐语林》的校证工作,特地编了《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唐语林校证参考书目》、《唐语林援据原书索引》、《唐语林人名索引》。试以后者为例,周先生说:“为了查对方便,我把每一条条文编了号,该条出于哪一种原书,查到之后随即记下。我把《国史补》等笔记小说原书,《太广记》等总集,《太御览》等类书,《能改斋漫录》等笔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一一翻检。有时看到某条材料,似乎与《唐语林》中某一条对应,但后者的条文有一千多,猛然要想知道它究竟在何处,可没有这种天分,于是我又把人名制成索引,一有疑惑之处,就查检人名索引,进行核对。笨人也就只能用笨办法来解决问题。”(《经验谈》第120页)实践证明编人名索引、文献目录这样的笨办法,往往是从事科研工作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
正因为周先生充分认识到目录索引对读书治学的作用,所以他非常重视对目录索引的编纂。如其《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就是在《唐语林校证》的附录《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的基础上加工成的。周先生曾对余历雄说:“我撰写《唐代笔记小说叙录》的目的是为爱好‘文史之学的读者提供一种可靠而便用的书目,希望当今的唐代文史研究者,除了注意正史材料之外,也要注意唐代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师门问学录》第25页,以下简称“问学录”)
为了提高文献的使用价值,他还注意为自己所整理过的书编制书目索引作为附录。如《韩非子校注》,周先生谈道:“全书将成时,我就希望有人来做一个人名索引,这是当代的学术著作必须具备的附录。但经多次提出,却无一人肯做。或许他们认为这类工作只有付出,对个人没有什么提高,故而宁愿闲谈消遣,也不愿动手的吧。不得已,我在统稿的忙碌之中,只能利用空隙时间,细加考辨后制成这一索引。”(《经验谈》第269页)再一个突出例子是《册府元龟》,周先生说:“我们古籍所整理的《册府元龟》点校本,早在三四年前就该整理好了,却因‘人名索引一项未能及时完成而耽误了出版。”(《问学录》第118页)可见,周先生对目录索引是多么重视。
二、 以文献学为基础
周先生说过:“不论从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献学与文艺学而言,还是从我后来提出的文献学与综合研究而言,都可以说明我们都很重视培育文献学方面的基础,而这正是继承了清儒朴学的优秀传统。”(《经验谈》第325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二中将清代朴学的特点归纳为十条,其第一条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其第二条为“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其主要方法就是考证,也即寻找与凭借可靠材料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周先生治学在以文献学为基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曾说过:“我的研究,一般都是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提炼。”(《经验谈》第414页)我们打开《〈韩非子〉札记》会发现有不少版本学论文,如《〈韩非子〉版本知见录》、《朱锡庚〈韩非子校正〉介绍》、《〈韩非子〉版本小议》、《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等。从中可见,作者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图书馆借阅过《韩非子》的各种善本,并对这些善本以及已有《韩非子》研究成果,作过深入探讨,还对《韩非子》做过艰苦细致的校证工作,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成札记,“在每一篇札记之内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至少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于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文集第1册第515页)。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全国编成大量法家读物,流传下来的却微乎其微。而经过周先生修订的《韩非子校证》与周先生所著《〈韩非子〉札记》依然一版再版,原因很多,其牢固的文献学基础,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周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献学修养,所以他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获得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并对其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欣慰地说:“正当我勤于寻找材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稀世之珍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与季振宜的《唐诗》,经恳切请求,才允许阅读。我就一鼓作气,读了半个多月,作了不少笔记,后来整理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应该说,这次偶然的访书机会,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其后也就与唐代文学?下了不解之缘。目下我正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主编《全唐五代诗》,就是由这一契机而深入这一领域的。”(文集第7册第361页)再一个突出例子是周先生1994年9月在日本天理图书馆看书时发现了二十三卷左右的唐钞本《文选集注》,遂将其复印后带回国。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在日本、台湾地区和国内各地尽可能地收集到一些《文选集注》残卷,于是辑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推动了《文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许逸民评价道:“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经验谈》第311页)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周先生还努力将自己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在《师门问学录》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关于版本,周先生说:“从校雠学的角度来说,著书并不以罗列版本为贵,而是应该将掌握到的版本梳理出几个系统,校勘之时,只要抓住几种系列之中的首出之书,也就可以执简驭繁,不致多岐亡羊了。”(《问学录》第103页)关于引文,周先生说:“撰写论文引用前人观点时,要注意两点:(1) 要引用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者之成果;(2) 要引用首出的单篇论文,不要转引后出的书。”(《问学录》第26页)这些经验之谈,是很难在教科书中找到的。周先生常用自己的治学经验与教训教诲学生,他曾举例道:“《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引周《清波杂志》曰:‘崇宁、大观间……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这是一则有关苏轼诗歌风靡朝野的生动记录。我要发表论文时,核对周《清波杂志》原书,却发现无此文字。随后我向人请教,也没有结果。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文字,却不可能贸然记得它的出处,我的论文因此延搁了很久都不能正式发表。后来,我翻检了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集笺注》,在书后的附录中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处:《风月堂诗话》。这类问题在《宋人轶事汇编》中很常见。因此,即使丁传靖已经注明材料的出处,我们引用时还是要重新核对原书。这种治学态度应当坚持。”(《问学录》第149?150页)他还指出:“关于材料的出处方面,还需要注意另一种情况:当我们阅读王国维、陈寅恪等名家的论文时,不能直接从他们的论文中摘引他们的‘引文。他们有时候只是断取,或概括大意,甚至是部分改写,并非原书的文字。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承清人遗风,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问学录》第150?151页)周先生还举例道:“我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时,起初就从陈寅恪的论文中直接摘引张籍写给韩愈的书信,后来核对原文,才发现陈寅恪的论文是将张籍写给韩愈的两封信(《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二书》)合成了一段文字来论述。幸好我能及时发现,及时改正,要不然险些就出洋相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问学录》第151页)
正是在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先生的不懈努力与培育下,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古典文献专业才形成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周先生曾说过:“我们这里的人写的东西水如何任人评说,而在文献的处理上还不至于有多少毛病,总想做到植根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决不望空立论,歪曲材料,甚或偷袭他人成果。”(《经验谈》第326页)
三、 综合研究
周先生治学的突出特点是综合研究。他说过:“我主张综合研究,为此我曾一再申述。”(文集第7册第372页)他还说过:“综合研究,锐意进取,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经验谈》第75页)所谓综合研究就是综合运用相关各学科知识来进行学术研究。
综合研究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周先生说:“我国向有文史不分的传统。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的教师,我是尊重这一宝贵传统的。”(文集第3册第229页)他还对“文史不分”的内涵作了如下说明:“所谓‘文史不分,从目下的情况来说,当然不能仅指文学、历史两门学科。我国古时所说的‘文史也不是这个意思。‘文史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哲学、宗教等等,尤与历代文人的有关,研究文学,自然不能不对此有所了解。”(文集第7册第371页)
周先生说过:“我一直主张综合研究,而在我的几种著作中,最能呈现这一特点的,要算《九歌》研究与李白研究。”(《经验谈》第63页)周勋初的《九歌新考》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显然得益于他的导师胡小石先生,他说过:“小石师年轻时就读两江师范学堂农博系,教师中有日籍教授多名,因此他在学生时代就能通日语。他博识多闻,阅读的范围很广,诸如宗教、民俗、神话、传说等方面的知识,无不具备。早在民国初期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就以人神恋爱的新说阐发《九歌》中的爱情描写,曾将《楚辞》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步入晚年,他又从事神话方面的研究,曾应南京市文联之请,作过一场《屈原与神话》的讲演,这些都是我在该一时期从他受业时的背景。”(《经验谈》第65页)所以周先生在撰写《九歌新考》时,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胡先生的研究方法,他说:“小石师的研究楚辞,就运用了宗教学、民俗学、神?学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我在他的指导下,研究楚辞,也就带有同样的特点。其后我把这方面的知识用到李白研究中,同样呈现出这些特点。因此,我所主张的研究方针是文献学与综合研究。”(《经验谈》第328页)
周先生的其他学术研究也普遍采用了综合研究的方法,如他在谈到《〈韩非子〉札记》时说:“这种写作方式比较活泼,内容不拘,只要有点滴心得,即可铺写成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为综合研究。目下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少见综合研究。”(文集第1册第2页)
周先生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实际上也采用了综合研究方法,作者在《后记》中说:“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着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希望能为目前尚不太为人重视的唐人笔记小说研究提供一些综合研究的实例,得出若干经过考核的结论,说明唐代笔记小说的学术价值,并阐述这一文体所发生的重大影响。”(文集第5册第314页)程毅中的书评《读〈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对此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把笔记小说提到与正史并重的地位,从文献史料学的角度,对它进行综合的认真的研究,那么所贡献于此道者,实以《考索》为多。”(文集第5册第319页)
现代学术研究分工日趋细密,如果学者联系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作综合研究,就可以对研究对象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周先生在综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學習与借鉴的。
四、 力求新颖,追求创辟
科学研究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所以创新是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征。周先生指出:“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人之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文集第7册第352页)他还说:“总的说来,文章论点当力求新颖,追求创辟。”(《经验谈》第396页)如果说周先生早年参加《韩非子》校证工作是服从组织安排,那么他撰著《〈韩非子〉札记》则是主动的选择。该书已充分体现了创新精神,作者尝云:“我在写《〈韩非子〉札记》时,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新见,至少要提出一些新的材料,段熙仲先生称赞此书为‘篇篇有根据,有心得的学术论文,恕不敢当,但自信每写一篇札记时,都曾说出若干新的道理来。”(文集第7册第352页)
周先生特别注意论文选题的新颖性,曾说:“我选题目,总想有一种新的视角,发人之所未发,希望能够取得‘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经验谈》第218页)如1983年5月,安徽亳县举办建安文学讨论会。周先生与会论文为《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论述了曹氏三世突破政治联姻的传统,娶出身微贱的女子为妻,甚至立为皇后,从而避免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他们的择偶标准重色而不重德,突破了两汉礼法传统。论文着重分析了曹氏家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指出:在曹氏家风影响下,“当时文人努力摆脱儒家的束缚,在文学上开拓新的领域,突出地表现在抒写军旅之苦与男女之情方面,而这正是建安风骨的重要内容”(文集第3册第35页)。该文让人耳目为之一新,颇受好评。
1989年6月2日至4日,在安徽九华山举行李白学会第2次年会。周先生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考证之风大盛,李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有人考察,取得很大成绩,我若于此再行投入,势难有大的开辟。若以‘多元文化的结晶的角度阐释李白的风貌与创获,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经验谈》第426页)。于是作者“在构思有关李白的文章时,觉得其子女的名字颇为怪异,本人亦颇有异端作风,遂列出几点,待日后慢慢写成一书:(1) 子女命名,(2) 籍贯与指树为姓,(3) 剔骨葬法,(4) 尊王攘夷,(5) 不崇儒,有战国余风,纵横游侠,(6) 从永王?乃必然,(7) 商人家庭,散千金,(8) 弃女人”(文集7卷末12页)。其与会论文为《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断》,随后又写了九篇论文,集成《诗仙李白之谜》一书。罗宗强在书评中称该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全解决,但却把李白研究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展现了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文集第4册第278页)。
周先生在古籍整理领域,也充满着创新精神。宋王谠撰《唐语林》是一本很好的书,也是一本很糟的书,周先生采用辑佚、校证、编辑等方法,尽可能地恢复了该书的原貌,并且还加了许多校勘记、注释与附录,如程千帆先生所说,此举是“救活了一本死书”(《经验谈》第123页)。他所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受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的启发,开拓了新的领域。他所辑的《唐?文选集注汇存》,为《文选》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他所主持的《册府元龟》点校工作,花了十三年工夫,使该书面目一新。全书十二册,最后一册为人名索引,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使用价值。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发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共计九十一种,周先生就有三种入选,“入选数量之多,独一无二”(《经验谈》第329页)。他所整理的古籍频频获奖,其中《册府元龟》点校本,还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凡此皆说明周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卓有成效的。
相关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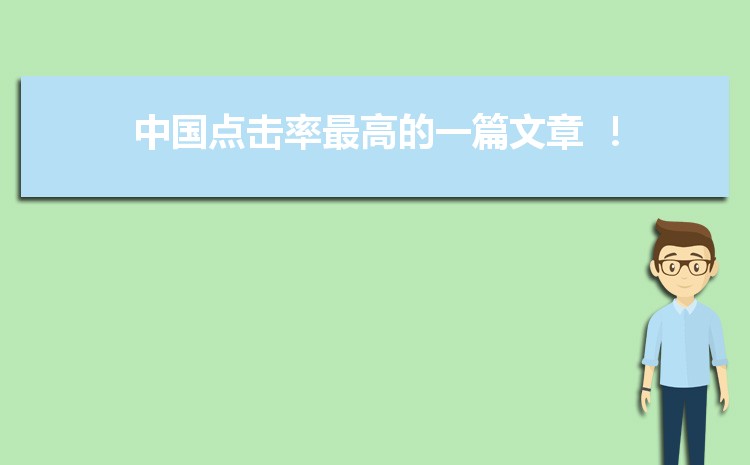 中国点击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1-12-23 01:49:29
中国点击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1-12-23 01:49:29  香港启思版《中国语文》初中教材写作训练的编排特点2021-11-14 01:24:42
香港启思版《中国语文》初中教材写作训练的编排特点2021-11-14 01:24:42  “古文字”知识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2021-11-11 04:25:23
“古文字”知识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2021-11-11 04:2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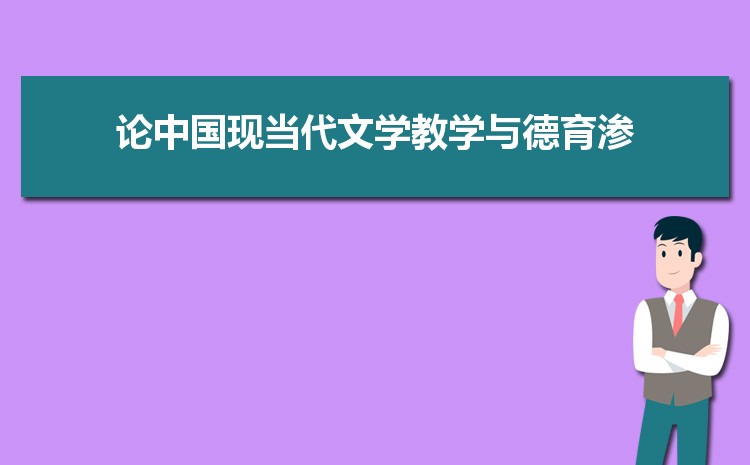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德育渗透2021-11-11 04:24:07
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德育渗透2021-11-11 04:24:07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40:02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40:02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8:43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8:43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7:02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7:02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6:26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6:26  保山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4:27
保山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学校口碑怎么样)2024-11-23 03:3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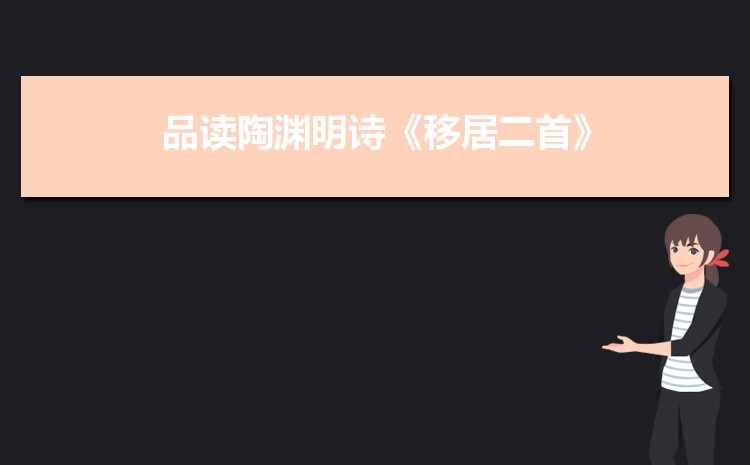 品读陶渊明诗《移居二首》2021-11-19 01:59:11
品读陶渊明诗《移居二首》2021-11-19 01:5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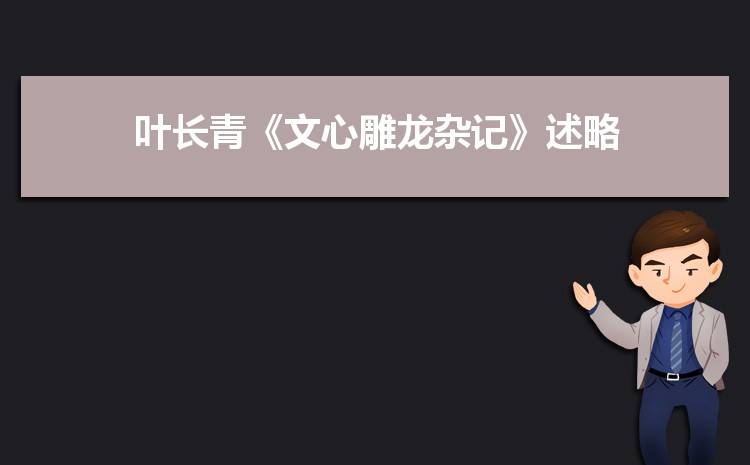 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述略2021-11-19 01:58:02
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述略2021-11-19 01:5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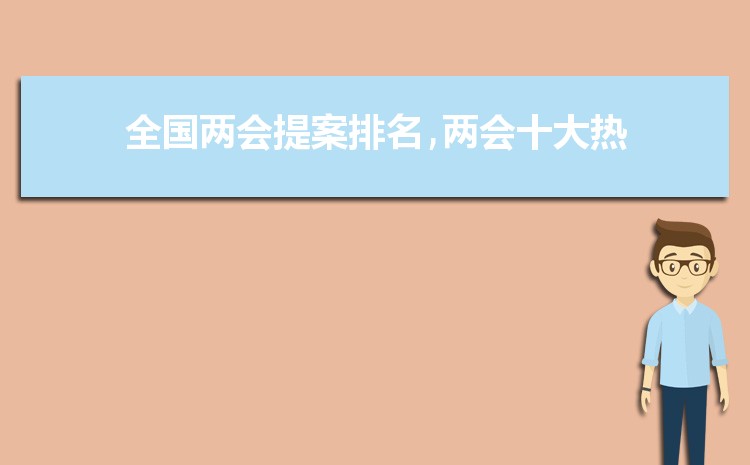 2019年全国两会提案排名,两会十大热点出炉了2021-11-18 07:58:12
2019年全国两会提案排名,两会十大热点出炉了2021-11-18 07:58:12
最新发布
图文推荐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
2024-11-23 03:52:06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办?
2024-11-23 03:49:47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现
2024-11-23 03:48:18
河北大学医学部是公办还是民办?(现在
2024-11-23 03:46:07
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是公办还是民
2024-11-23 03:44:36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
2024-11-23 03:42:42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民
2024-11-23 03:40:02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公办还是
2024-11-23 03:38:43
